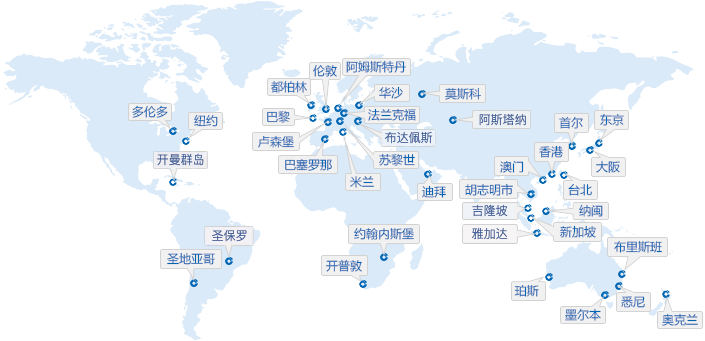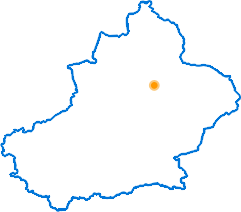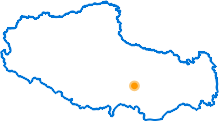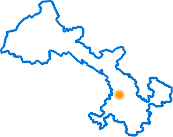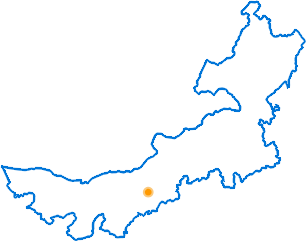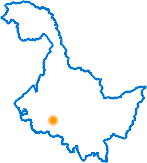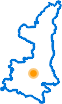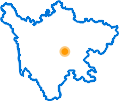|
唐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四面楚歌”的存在,却又刻意将它们隔开一段距离;他讲述的,是一个像他这样的阅读个体,何以“把自己丰盈且辐射性的感官给封闭起来,宁可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成为一个(与身外世界)无关系的人”。 《纽约客》漫画:“哇靠!原先住在这里的究竟是哪种疯子?” 仿佛只是一夜的秋风乍紧,我便感到书业里透出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味道了——看着扰攘喧腾,实则萧瑟衬底。书店的前景似乎已无争议,也许不用过多久,哪家居然仍在惨淡经营,倒反而会成为新闻。至于电子书对实体书的围剿,美国《新闻周刊》已经用上了如此惊悚的标题:Does one have to win?(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吗?)——尽管细看内容,到结尾仍是举棋不定,并不敢判定你死还是我活。于是从书架上找出所有与“阅读”有关的书——《阅读史》(阿尔维托-曼谷埃尔),《阅读的历史》(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卡萨诺瓦是个书痴》(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嗜书瘾君子》(汤姆-拉伯)……说好听点这是祭出家法壮胆,但说白了,这难道不是在徒劳地赌气,抑或掩饰类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拷台小姐的失业恐惧症吗? 这堆书里当然也包括新近在内地出版的《阅读的故事》。我翻翻,发现作者唐诺居然已经为我的这些举动写好了辩护词:“阅读会因为意义的丧失而绝望难以持续,然而,意义最丰饶的生长之地却是在书籍的世界之中,人的原初善念只是火花,很容易在冷冽的现实世界空气中熄灭,你得供应它持续延烧的材料,我们眼前这个贫瘠寒凉的世界总是货源不足,因此,阅读要持续下去,它真正能仰赖的就是持续不回头的阅读。” 持续不回头。能驱散对阅读之绝望的只有“阅读”这种行为本身。好吧,继续翻下去,这本书里持续闪烁着点点萤火,不时读到心里微微一亮。好比这句:“我跟书店的关系后来变得挺麻烦的,同时拥有着如电池正负两极的身份——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但凡像我这样身份不再单纯的读书人,读来都是会涩涩地一笑吧。其实岂止是对书店,自从供职出版圈,对图书生态系统里的一草一木,大到一场书展小到一条腰封,都凭空生出正负两极,于是懂得老鼠跌进米缸里,未必就是一味欢喜。这心态,在《阅读的故事》里,淡然道来,刚好到达略微激起业内“同此凉热”的程度。唐诺既非信息密集型亦非情感澎湃型的作者,下笔有踌躇,行文多迂回,要慢慢读才能读出趣味。耐人寻味的是,就本书主题而言,这样一步三回首的叙述气质,倒正契合如今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阅读”本身。 这问题得从头说起。如同所有具备深远历史背景的事物一样,构成所谓“传统阅读”的诸般要件,其实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好比说,我们如今早已习惯了默读,习惯用视觉(整字 / 词甚至整句认知)而不是非要依靠分解语音才能理解语义,因而无法想象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上千年)里,创作者一直设定他的作品是被“听到”而非“看见”的。有研究报告辩称,在人类的进化中,大脑为默读功能辟出专区是晚近才发展出来的现象,且此现象目前仍处于演变之中,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中世纪的著作正文里,还不时会出现呼吁听众聆听故事的字眼。按《阅读史》的说法,那时,书页上的文字在眼睛感知它们的时刻并非单单“变成”声音,它们本身就是声音。曾经,无论是修道院里的缮写房,还是那座似乎只存在于传奇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些掌握了珍贵的读写能力的智者,都必须借助于高声朗读,借助铿锵的音节,才能真正地“吞噬”乃至“消化”文字。除了生理上可能存在的局限外,观念是另一个重要障碍。苏格拉底就曾以“文字如果遭遇虐待或滥用,往往需要仰仗其父母(作者)的帮助,文字本身并没有自卫与自救的能力”为由,坚持口述传统,拒绝将自己的思想形诸文字(这跟当时的书面语相对粗糙也有关系)——写下思想,被他人朗读便是虐待或滥用,若读者竟可以默会于心,任性阐释,则更不啻为一道“作者已死”的宣判令了。 事实上,拯救文字被误读的冲动,至今仍潜藏在西方作家的意识形态中,许多重要作品都有作者亲自朗读的录音版本出售,作家朗读会更是在各类文学节上公开售票的保留剧目,从狄更斯到卡波蒂都是以非凡感染力遐迩闻名的朗读明星。另一方面,在当权者和正统人士看来,默读的可怕之处更在于,“一本可以私下阅读的书,一本只用眼睛便能阐述文字意义的书,不必再聆听当场阐明或指导,非难或审查。”(圣奥古斯丁:《忏悔录》,VI,3)……理解了这些背景,也就能够明白,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里如草蛇灰线般时时提到的那两个字眼——“自由”(“如果我们不尽恰当地将书籍比拟成某种动物,找寻它维生的最主要食物,那大概就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我个人坚信,一个好的阅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应该都拥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干净灵魂”),确实是理解现代阅读方式的关键词。 再比如,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当然直接促成了阅读史上最大的“私人化”革命,但我们可能低估了照明条件的改善和眼镜的发明在两侧“煽风点火”的作用。苏美尔书记员在昏暗的光线下,把小小的泥板放在盛满清水的透明杯子(幸好玻璃器皿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已经出现)后面,用来放大楔形文字的年代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于是,开本和字号越变越小,排版越来越照顾信息量(而不是为了降低阅读难度),就成为可能。无数诸如此类的细节与人脑机能的发展、视神经细胞的敏感度乃至科学家们至今无法详尽阐释的人眼攫取信息的方式形成循环互动,这些阅读历史上的蝴蝶效应经过多年磨合,最终使得载体与内容与思维发展踩着同样的舞步转圈前行。而舞步所到之处,便勾勒出唐诺所说的“阅读的整体图像”,“一个人类不无侥幸成分所艰苦创造出的独特基因之海”。 但是唐诺在“基因之海”后又用了个破折号将笔锋一转:“——科学的进展太快了,事隔几年我已经不敢确定这个举细胞生物世界的基因交换取用说法是否还成立……”我理解他的这种犹疑。正因为创建阅读的整体图像的过程如此“不无侥幸”,所以,迅速挪换掉其中的任何一块拼板,都叫人痛惜、恐惧阅读的未来,担忧一旦惬意地躺上科技流水线,便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没错,从石头到泥板到莎草到竹简到毛皮到纸浆到薄如蝉翼的屏幕,从手抄到印刷到几分钟搞定的下载,介质越来越轻,渐近于无。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得到的是信息的海量扩容,是知识财富的涓滴效应,是阅读人口和写作人口的高速膨胀,是一器在手、坐拥书城的幻象,是被超文本的视觉语汇大大拓宽的认知幅度——但是,为什么那个向来喜欢乌鸦嘴的菲利普-罗斯要痛心疾首呢?他认为,即使以最乐观的心态预测,只要再过二十五年,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将成为只有少数狂热信徒膜拜的异教——“也许要比现今读拉丁文古诗的人多一点点。”就像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感叹印刷术令建筑记录历史的功能全面消亡一样,罗斯认为必将摧毁小说的是大大小小的“屏幕”。这些屏幕让获得信息和故事变得那么容易,那么支离破碎,以至于将来我们会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群体,能在一长段时间集中精力投入阅读”。 当事情变得多少有些伤感的时候,我也许该插播一段自创煽情体:捧起一本书来,你真的以为只是在读书里讲的故事吗?经过某个拐角书店时瞥见裙裾一角,进而买下了那本与裙子的颜色格外相称的软皮书,单手握住书脊处微微让虎口感到的酸,另一只手摩挲纸页纤维,于掌纹间留下的或光滑或粗粝的印象,抑或是一个皱巴巴的猫耳折页,一条洒上泪痕或茶渍的划线,一本书在书架上、床头柜边、厕所里的摆放位置,充盈在鼻腔里的某种胶水气味,藏在课桌洞里、包在粉色禁书封皮外的挂历纸,某张随手夹进消遣小说里的人民币,甚或痛切的、遗忘在火车车厢里,不得已重买一本,却再也没兴致看完它的往事……我想说的是,以上种种,都是潜在作用于你的阅读记忆的暗流,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循环在故事外的故事,帮助你完成阅读的最高使命:抵抗遗忘。再仿真的电子阅读器,面对这些或许已经神秘地编入基因密码的诉求,怕是都要力怯气短吧。问题是,明天的读者,还会觉得这些是重要的吗?未来的我们,还需要抵抗遗忘吗? 一味悲观是没有意义的,毕竟,阅读的这一路进化本来就在沿途扔下不少东西——包括苏格拉底的抗拒和雨果的叹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理论上,多维的泛阅读时代,应该能提供更多的建筑材料,修建更宏伟的文化巴别塔。有专家指出,电脑阅读的屏幕滚动方式很像徐徐展开莎草纸卷(竹简),这可以算是某种形式主义的返祖现象;电脑为作家与读者提供更先进的互动平台,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捡回口述时代不断根据反馈修正故事的传统。沿着电子化指引的方向,对未来读者的漫画像大抵是这样的:他(她)“在电车上以自慰般的手势抚摸iPad”(宫崎骏语),那里储存着一个实时更新的小型图书馆,随手翻开某一本,不管点开哪个词都冒出一幅图片、一串链接来,他(她)早就习惯于被它们分神,也知道这本书照例不会看完。看不看完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人类文明的碎片已如蛛网般密布在他周围,任何知识都触手可及、彼此勾连,那时候,连续的、纵深的、肉感的、整块整块结结实实的、每跨过一个逻辑点都需要反复推演的思维模式,就跟曾经储存过它们的面貌各异的书籍一样,只有在古董店里才能须臾亲近。他(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因为“阅读”这件事本身,也正在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完善,将主动吸收信息的方式全盘置换成被动接受。超文本链接,云计算,模糊搜索,图像识别……“电子书”的下一波潮流可能是大踏步地跳过古人(二十一世纪前的“古人”)的记忆环节——也许,阅读的终极目标就是抛弃“阅读”,数据通过电子脉冲,源源不断地灌入大脑……记忆和思考的过程,将由此变得不那么艰辛,当然,也不那么快乐。 这担忧,若隐若现地渗透在《阅读的故事》里,但还好,不泛滥。它们只是这本书的不需言说的潜台词。唐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四面楚歌”的存在,却又刻意将它们隔开一段距离;他讲述的,是一个像他这样的阅读个体,何以“把自己丰盈且辐射性的感官给封闭起来,宁可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成为一个(与身外世界)无关系的人”。也因此,初看《阅读的故事》的目录,会觉得有那么点我行我素,落伍悖时。都什么时候了,作者还在认认真真地讨论“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还在兢兢业业地诱惑人们“也要读二流的书”,还在细细碎碎地缅怀查林十字街八十四号里的温暖夕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布着传统阅读之道。是要读到最后最深处,才能省悟,这姿态本身便是最好的布道词。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体所说——“如果将一个人阅读《哈姆雷特》的感受逐年记录下来,将最终汇成一部自传。”——对个人而言,“阅读史”固然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发展史,对自己有意义的那部分却只与“心灵史”接通,勾勒着自己与书本相识、热恋直至携手老去的过程。当心灵倔强地听命于自己编写的历史时,哪怕逆向行驶,哪怕“唐”臂挡车,你也可以微笑着往前去。(东方早报) |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 建行客服
建行客服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