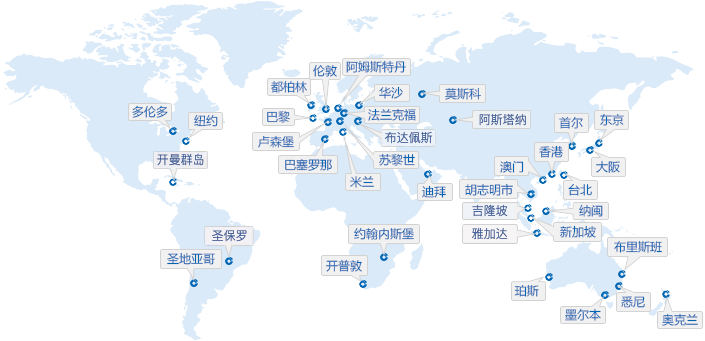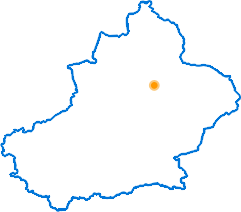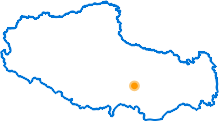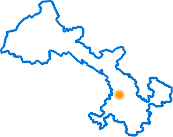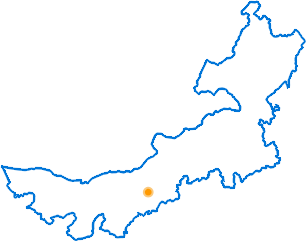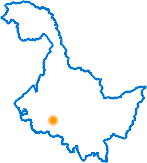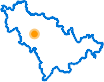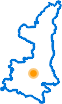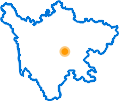|
《风语》 麦家著 金城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早在麦家的这部新作品还没写完时,关于它的“风言风语”就已经满天飞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谈论该书稿酬或影视作品的新闻就“刷刷”地跳出来,多得可以刷屏;但另一方面,在《人民文学》用连续四期连载完第一部之后,我却没能找到一篇关于此书的文学评论。也就是说,《风语》的流言很多,但以文学的态度严肃地看待《风语》的,目前却很少。我想,这对作者也是一种不公平。 手艺是写作的重要才华 《风语》讲述的是中国黑室的故事。黑室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设立的神秘部门,“美国密码之父”亚德利曾在那里工作过。主人公陈家鹄是一个数学奇才、天才破译家,在目前看到的第一部里,主要是围绕着他进入黑室前后的故事来写,一系列把他作为目标的暗杀和保护行动,正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的。 《风语》虽没有人物原型,但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可以扎进历史中去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庆,多方力量在此角逐、暗战,这些代表不同政府、不同利益的力量互相制衡、互相利用,甚至试图置对方于死地。书里忠诚地再现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多条线索平行交错、齐头并进。在这里,数学家陈家鹄是一条线,美国密码之父亚德利又是一条线;黑室主人陆从骏、杜先生是一条线,地下共产党李政、天上星等人又是一条线;美大使馆内的通日叛徒萨根是一条线,日军情报人员少老大及手下冯警长又是一条线。甚至还不止,包括陈家鹄的哥哥陈家鸿、萨根的姘头汪女郎等,都站在不同的立场,都代表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就算在同一阵营里,每个人也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书中对他们的性格、背景、动机等,有体贴入微的交待。 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就血肉丰满了,除了主动脉,还有诸多毛细血管,阡陌交通,有条不紊。作者建架了一个宏大而精细的体系,如何编织这些人物关系、如何安排故事经纬线,显然是一个十分精巧的技术活。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老话题。麦家被有的评论家认定为类型小说作家,但在读过他的几部小说后,我觉得这种说法只不过是题材决定论。事实上,从《解密》、《暗算》到《风声》、《风语》,麦家这几部小说的写作手法都是有明显变化的,结构和语言风格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蔓延生长。 同时,我也相信,技术活就是最难的活。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懂得手艺就是写作最重要的才华之一,能把故事讲好,是一个优点而不是缺点。 解密是绞灭天才的方式 当然,《风语》所写的仍是麦家所独有的“解密”题材,体量庞大,却针脚绵密。他对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推进过程中所特有的苦难命运,显然是感同身受的。他多次谈到写这部小说之苦——体力上的、精神上的。在我的理解中,不仅是因为这本书篇幅巨大,消耗体力精力,更是对人的无能为力感觉到了某种痛楚。 书中,有几个例子给我深刻印象。比如,陈家鹄解开21师的密电,是一件非常侥幸的事:他选用了一种已经退役、落后于时代的“指代密码”来破解。他的解释是,日本是一个守旧与创新相结合的国家,说不定会用这种旧的密码。然而,真正的理由是,只有这种方式能在短时间内试一下,而正常的破解方式根本来不及——结果,日军真的就是用了这个早就被认为没有价值的密码。他们又一次成就了奇迹。 很显然,在这里,密码的破解要凭智慧、凭分析,更要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运气。所以,麦家一再强调,解密码太残酷了,是绞灭天才的方式,是对人的智力的毁灭方式——解不开,是正常的;解开了,是神迹。 所以,他不强调陈家鹄令人惊叹的破译能力,却常宣扬解密之不可能;不写“黑室”的强大和劳苦功高,却常感叹萨根、少老大等反派的狡猾能干;我方获胜时不写其精密布置之良苦用心,却常抒发取胜之侥幸和意外。整本书里充满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吊诡。 其实,何止是解密工作,革命、战争,对人性的辗压何尝不是到了疯狂的地步。陈家鹄被“正义”胁迫着参加破译(也就是战争),摧毁了他的人生,拆散和毁灭他与妻子的爱情,这绝对不是他的意愿,可是,他别无选择。只要不同意,就是民族罪人。战争让这个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也放不下一张温暖的饭桌。正常的人伦早被残酷的现实发配到国境之外,甚至离开中国也不可能得到和解;人也只能异化为一颗大局观下的棋子,变成刀俎上的鱼肉,任命运宰割。 他们是真正有灵魂的人 麦家最近有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不惮想象人的弱,却不敢想象人的强”,说的是人性弱点、世态炎凉。但我觉得换一种意思理解更合适:人是非常脆弱的,不过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风大一点就折了。人虽然有思想有智识,但他的强,却往往是命运和上天造就的,而非人力所为。麦家没有高估人的智商,哪怕是他写的已经是最聪明的那群人了。我想,麦家所表现的这种人力之“弱”,其实就是一种对上苍、对命运的敬畏。他与诸多《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本质区别,就是从来没有谵妄,从来没有意淫,自以为人定胜天。 即便如此,他心怀悲悯,仍决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些向着“不可能”而迈进的主人公,就是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赫拉克勒斯,走出迷宫的忒修斯,也是盗来天火自我牺牲的普罗米修斯。他们都是英雄。在麦家的笔下,这些英雄都有些非正常人类的偏执气质,无论是《解密》里患有幽闭症的容金珍,《暗算》中单纯得可笑的瞎子阿炳,为世俗所不容的黄依依,还是《风语》里与革命气息格格不入、自私自我的陈家鹄。 对这些异人,我所最钦佩的并不是他们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而是他们敢于在全民一致要求革命、要求献身、要求纯洁、要求神圣的氛围下,还尽可能地倔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个性。事实上,看到那些从来不需经过思考就能英勇献身的勇士,我对他们的怜悯总是多于尊敬:正如茨威格所说的,“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革命至上,就一定比爱情至上或家庭至上更高贵吗?我看,不见得。像陈家鹄或黄依依们,人虽然被收编到组织中,但他们始终抱着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革命至上把爱情或家庭看作他们在难以逃脱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思考,圈起自己内心的小小世界;他们才是真正有灵魂的人。 可悲的是,在战争年代革命年代,恰恰是最不需要灵魂的;越是有思想的苇草,越是会成为大风所摧毁的目标。这本书只出了第一部,陈家鹄后面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但我不相信他能侥幸逃脱;也许是肉身的伤害,也许是信念和世界观的彻底瓦解,总之,他不可能得到时代的宽囿。我们向来都是这样对待英雄的。是以,我格外地期待《风语》的第二、第三部;看看英雄是怎么成长起来的,革命,又是怎么把一个人的爱情和人生辗得支离破碎的。(南方都市报) |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 建行客服
建行客服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