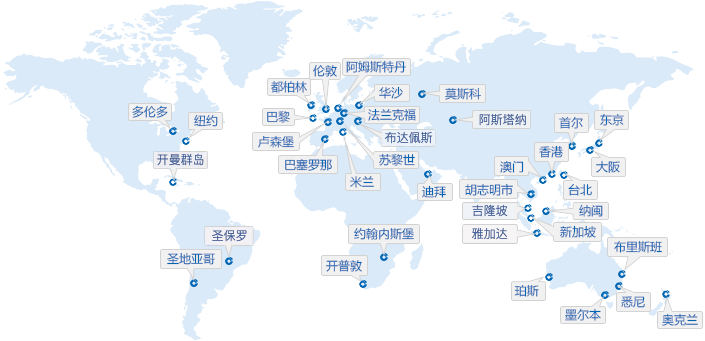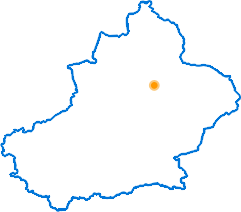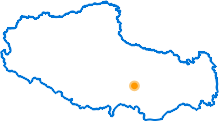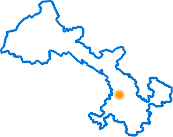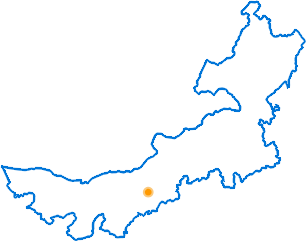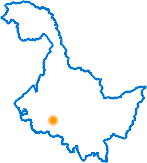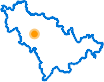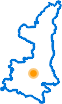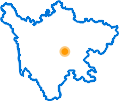|
克拉科夫太古老了。 两天的克拉科夫之旅,仿佛逆时光而行。如同行的朋友所言,一个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或者柏林快要失去的欧洲,我们却意外地在克拉科夫相遇了。 曾经的欧洲三中心之一 从华沙到克拉科夫,三个小时的火车,一路穿过平原与森林,仿佛带着我们从都市向乡下返回。克拉科夫常住人口76万,从地图,或从数字上判断,它如此之小,甚至难企及中国一个边缘地区的小县城,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来,欧洲及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迫不及待地改变着自己的面目,唯有克拉科夫未变,它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依然围绕着周长 克拉科夫古城有7个入口,中央是Rynek Glowny广场,从公元7世纪至今,一众教堂、修道院、钟楼、方塔、联排住宅和贵族府邸始终如一地保留着,如同一部古典的欧洲城市史。在雨雾迷蒙的早晨,我们沿着石板路来到广场中央,在一丝陌生的细微震撼中,我仿佛找到了一些熟悉的记忆。的确,我记起来了,在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两生花》的镜头里,主人公维罗妮卡选择在这里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相遇。那是一个永恒的镜头,它缓慢地叙述,掠过塔尖上的天空,像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梦境。 站在Rynek Glowny广场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远不只梦境般的艺术,还有如今这里的人们那充满“过去式”的缓慢的真实生活。 清晨,圣玛丽教堂的钟声响起,在广场四周的联排住宅和贵族府邸里,克拉科夫人开始活动了,他们向广场上的中央市场围拢过来。这个市场有700多年历史,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上下两层,曾经它的名字叫织物馆(Sukiennice),据称是16世纪大半个欧洲的购物天堂。此刻,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正在进行外墙整修,如今它已不再出售16世纪东欧那浓艳的木制品、刺绣或皮革制品了,取而代之的是马祖尔湖区的蘑菇、克拉科夫地道的小麦面包、波罗的海红鲱鱼,或者一些花卉与瓷器。像克拉科夫人一样,我在一位克拉科夫大妈的指导下,用嘴唇抹了抹洋葱汁,第一次像个鸭子一样张开大嘴“生吞”了一条肥硕的红鲱鱼,算是克拉科夫的早餐。 正如其他欧洲城市一样,教堂总是城市的中心,而在以天主教为主的克拉科夫,圣玛丽教堂也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所在。这是一座双子教堂,一高一低,以其繁复的哥特风格闻名于世,当我正以一种饱满而好奇的热情生吞红鲱鱼的时候,教堂里传出一阵嘹亮的小号声。 据说,圣玛丽教堂如今每逢正点不仅要吹号报时,还要在演奏中出现“休止音”。这是克拉科夫的一段悲情历史,也是波兰悲情历史中最典型的一段。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欧洲,当奔袭至克拉科夫时,被正在教堂塔楼的吹号手发觉了,他们一箭射杀了号手,但正在进行的演奏戛然而止,引起全城军民的警觉,他们同仇敌忾打退蒙古军的这一次进攻。为了纪念这位号手,圣玛丽教堂如今每逢正点不仅要吹号报时,还要在演奏中出现“休止音”。 除了科隆大教堂外,据说在欧洲北方,这座教堂算是最宏伟的了,尤其是教堂里面的总祭坛,绚烂之极,超越了一切物质上的奢华与唯美。我们不是信徒,是那种出现在世界各地,每到一处都要举着相机照相的观光客,但在克拉科夫圣玛丽教堂前,怀着对神圣的尊重,我们没有抱着相机随着那些早课的信徒挤进总祭坛前,而是站在外面听着那优美而陌生的赞美诗从风中传来…… 这么说吧,克拉科夫是一个圣徒之地,作为一个观光客,你觉得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欧洲:怀旧、古典、神圣。几百年来,它几乎一直如此,无论是它的城市建筑风格,还是生活节奏。在教堂外面卖卡片的地方,从卖卡片的店主那里,我们才会蓦然知道,曾任梵蒂冈大主教的保罗二世就曾出生并生活在这里,在这座城市,他最终形成了对信仰的真理认识。 波兰人一直把克拉科夫称为故都,在华沙或其他城市工作的人,克拉科夫总是他们疲惫不堪时最好的去处或归宿,周末来圣玛丽教堂祷告,或来克拉科夫举行婚礼,这是一种波兰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周边诸多东欧人的生活方式。 公元700年,波兰在此建都,14至16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克拉科夫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它曾与布拉格和维也纳三足鼎立,成为欧洲三大文化中心之一。一切都在流逝,如今,欧洲正滚滚向前,而克拉科夫以独特的姿势保留着它的过去。 诗人生活之所 实际上,克拉科夫成为波兰的故都,不只表现在地理上,而且也在心理上与文化上。可以说,1000多年以来,克拉科夫始终是波兰人精神上的皈依,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坠机事故之后,最终也选择在克拉科夫举行国葬,因为只有这里才是波兰精神上的神圣家园。 在克拉科夫,我总期望能在一个咖啡馆碰到一位性格忧郁的女诗人,几乎每天她都要在那里写作。她就是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博尔斯卡,她选择生活在一个76万人的小城,选择在一个在精神上始终与过去保持着一致的故都。当然,在那两天里,我没有那么幸运,没能在那家咖啡馆遇到她。但在拜访克拉科夫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雅盖隆大学时,在大学博物馆里,我见到了诗人辛博尔斯卡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枚金质奖章,因为“在观察世风百态时心灵郁结的愁绪和高逸脱俗的清冷情致”,辛博尔斯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那枚小巧的圆形金币面前,我感受到了长久的震撼,它甚至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波兰式的精神。 辛博尔斯卡与另一位中国读者熟知的波兰籍诗人米沃什(他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他们的晚年都选择了生活在克拉科夫,在那里生活与写作。辛博尔斯卡将这枚金质奖章捐献给了这座古老的大学,它被保留在一间小小的大学图书馆里,她认为这一切皆因克拉科夫所赐,是这个城市所代表的欧洲精神的荣耀。 的确,诗歌、宗教、音乐在克拉科夫是“三位一体”的。在古城Rynek Glowny广场上,有一尊青铜雕塑昂首苍穹,矗立在圣玛丽教堂对面的广场中央,它是波兰民族诗人密支凯维奇的塑像。密支凯维奇之于波兰,就像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惠特曼之于美国、歌德之于德国一样,是民族语言的开端,更是民族精神的开端,在众所周知的多灾多难的波兰历史中,密支凯维奇的诗篇就是照亮历史的火炬。 当然,在短暂的两天行程中,我无法更多地深刻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也无法更多地从这些诗人、圣徒们的故事中获得他们古典而优雅的精神谱系,作为一个过客,我只能说在克拉科夫,我与古老的欧洲曾偶然相遇。(第一财经日报) |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 建行客服
建行客服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