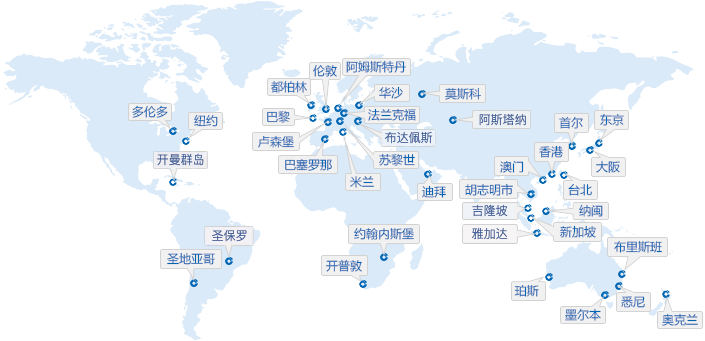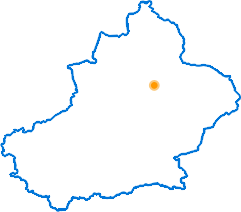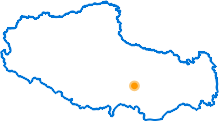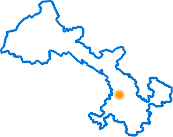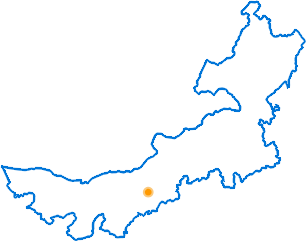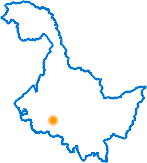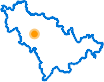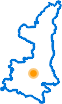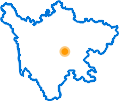|
《布努艾尔谈话录》 [西]布努艾尔 [墨]科利纳 [墨]图伦特著 何丹译新星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无比珍贵的口述史 不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超级影迷,大约对路易·布努艾尔都有些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的名头和口碑都毋庸置疑,但想成为他的拥趸——尤其对于远离欧洲正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件难事。布努艾尔的影片不像新现实主义那般直白有力,不像作者电影那般让观众有着强烈的代入感,更不像小津或奥逊·威尔斯那般有着风格独到的电影语言体系。他的很多影片只可意会,却不可言传。因而,关于布努艾尔的研究专著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其准确性也令人生疑。由此来看新星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布努艾尔谈话录》一书,是大师人生中的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遗产”。时值布努艾尔诞辰110周年,此书的问世也为我们进入他神秘丰富的艺术世界打开了一道狭窄而透光的门。 据说,布努艾尔毕生对于采访都存在着“交流障碍”。他的合作密友、法国著名编剧让-克洛德·卡里埃曾说:“但凡电影记者都知道,要从他的嘴里撬出几个字来是多么困难,而且,就这么几个字还往往是在嘲弄和打趣。”1981年,就在布努艾尔去世前两年,卡里埃千里迢迢从法国飞到墨西哥,说服年逾八旬的布努艾尔开始书写自传,这便有了后来广为影迷所知的《我最后的叹息》。此书影响极大,至今在内地已经至少有了三个版本。 就在布努艾尔伏案自传的时候,另外一部有关他的对话体著作却还在艰难的修改整理中,这便是两位青年电影评论人图伦特和科利纳采写的《谈话录》。其实,这本书最早的筹划在1974年就开始了。两位年轻人当然知道布努艾尔对访谈有抵触情绪,于是采用了迂回战术:先与布努艾尔成了忘年交,陪同他上电视,还经常在一起聚餐。酒桌上最好谈事儿(中国人应该深谙这个道理),于是在一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布努艾尔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采访从1975年初开始,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总共五十多个小时的谈话,涉及布努艾尔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谈话录》最后出版的时候,布努艾尔已经辞世,因此这也成了他此生唯一的一次对个人作品的全面回顾。 “安达鲁狗”和波希米亚生活 我估计很多读者看这本书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就是想知道大师如何为自己“释梦”,譬如那部困扰了大家八十年的《一条安达鲁狗》(1928)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部16分钟的超现实主义名片是布努艾尔与画家达利合作的,它的影像十分晦涩,但仍然被后世评论家划入“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列——因其率先运用了象征、省略的影像和印象主义的剪辑技巧”。 但布努艾尔却是个打太极的好手。正如图伦特所说的,“布努艾尔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理论化的导演。……他常常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完全不让我们探究他的内心”。布努艾尔的记忆力很好,在谈到《一条安达鲁狗》时,他坦言拍摄“挪用”了母亲给妹妹的嫁妆钱,那个人眼被刀割开的镜头其实是用一只小牛眼代替的,而影片在巴黎首映时他躲在幕布后面、手持石块时刻准备对挑衅的观众进行“超现实主义式的反击”等等。同时,他又对所谓“安达鲁狗”是用来指涉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说法矢口否认,指出这只是自己写的一本诗集的名字,而电影原本要取的名字则是《切勿把头伸出来》——这也正是《谈话录》的那个令人费解的副标题的来由。 布努艾尔、达利与洛尔迦的三人关系,一向是影史上时常被谈论的话题。2008年,英国拍了一部叫《少许灰烬》的影片专门来讲这三人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片中以洛尔迦为中心,叙述了他与达利之间一段隐秘的同性罗曼史。布努艾尔原本与洛尔迦惺惺相惜,可当发现二人的不伦之恋后极为恼火,时刻想拆散他们。他拉走达利去巴黎拍摄电影,但两人的合作亦在次年的《黄金时代》后便匆匆结束,三位分道扬镳的艺术家此后开始了不同的命运之路。 历史真实总是比缠绵的情节剧更加混沌复杂。在《我最后的叹息》中,布努艾尔曾对洛尔迦的同性行为予以否认,但我们却分明可以察觉到布努艾尔确实有着强烈的恐同情结,这种恐惧甚至就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譬如图伦特在《谈话录》中所回忆的,布努艾尔讨厌被采访,正是因为他“害怕那种叫做‘录音机’的电子设备,以及‘阴茎’(他的原话)似的话筒”。我想,这正是本书最有意义的地方,尽管口述方式出于受访者的复杂动因或“为尊者讳”无法实现完全客观,但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点滴的缝隙中寻求他的心灵变迁。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洛尔迦被右翼弗朗哥政权的长枪党秘密杀害;而布努艾尔则被迫再一次去国怀乡。虽然今天我们经常称其为“西班牙电影大师”,但其实布努艾尔一生只在祖国拍摄过4部影片(其中多部被禁),他的艺术轨迹辗转于西、德、美、墨、法等诸多国家。布努艾尔是彻底的波西米亚人,一生过着漂泊自由的离散生活。 真相无始无终 这本《谈话录》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修正了很多我们对于艺术大师的臆想。在很多人眼中,大师们从来不食人间烟火,只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实际并不完全如此,布努艾尔在谈到《女仆日记》(1963)时便说,他也想拍让观众喜欢的商业片,“我很清楚影片是有投资的,涉及很多人的工作,需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同时,有影迷从《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这类讽刺批判性影片推测,布努艾尔是站在有产者的对立面上,实质上老人也坦言,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审慎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关的东西并不都是糟粕,总有些精华被保留下来。 当然,布努艾尔的很多电影没有真相,也没有答案。这些令人困惑之处,构成了电影的原生魅力。书中结尾之处,两位采访者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欲望的隐晦目的》(1977)中女主角背上的袋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布努艾尔狡黠地笑笑,反问道:“你觉得呢?”采访者说:“会不会是《一条安达鲁狗》中主人公用绳子拽出来的东西?”老人不置可否,书也就此结束。其实,布努艾尔的艺术构思有很多这样的“圆形结构”,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无休无止,用老人的原话说就是“一切无需解释。我们只要知道:它们是否让我们反感,是否打动、吸引我们。这就足够了。”(南方都市报) |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 建行客服
建行客服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