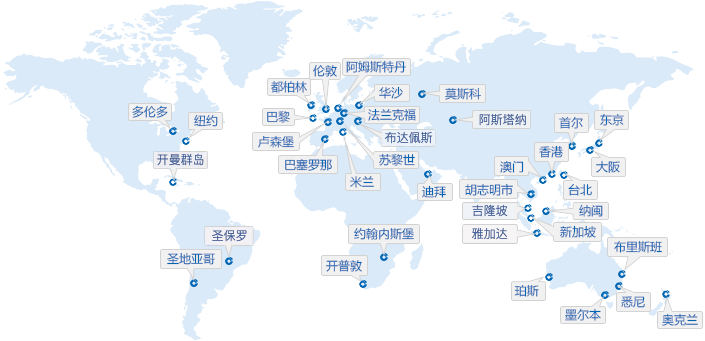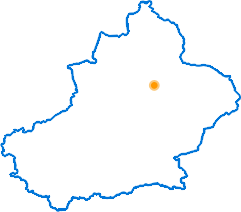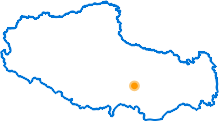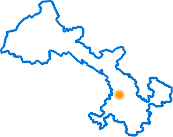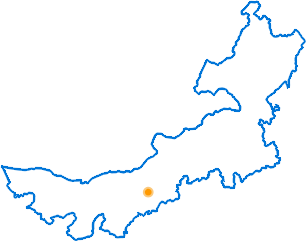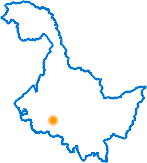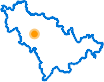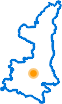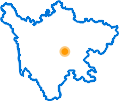|
这个小标题,是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出版社)的副标题。因作者与中国关系非同一般,这本意味深长的著作,得以顺利出版。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清的故事,即使在中土,亦流传甚广。佩雷菲特的这本大书,比之他先前的《官僚主义的弊害》,此后的《信任社会》,都要受到关注,因而多次再版。但我相信,其重要性,远未被我们认识。“两个世界”的提法,极为关键,却被平平看待了。 “两个世界”,指的是中国和西方:处在欧亚大陆两端,被天然屏障和另一个世界(伊斯兰化的波斯帝国)隔开了。历史上,它们少有往来,彼此互不相识。明清两代,东来的传教士,将中土信息传递给西方世界,从而构造了西方对中华帝国的想象。事实证明,想象多有失真。即便如此,那个世界到底开始认真打量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毫无兴趣。 是时,西方世界的工业、科技和贸易革命,打破了这个世界对其毫无兴趣的状态——你感不感兴趣是你的事,我是否一头撞上你,则是我的事。两个世界的心态,在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不是相撞,而是西方世界撞进来了!这一事态及其进程,最有意义的追述的开始,正是马戛尔尼使团访清。 以后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 这个开始,到底怎么回事,西方世界投入的研究力量,是我们无法比拟的。当然,两端的解释,更是大相径庭。《停滞的帝国》是西方解释得比较典型的代表意见。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旨趣——千年中华帝国,其存在状态是“停滞的”。这样定义时,作者心目中,所用来做比较的刻度的另一端,自然是“活跃的”,事实也是如此。 你可以对“停滞”和“活跃”,做任何意义上的发挥,但事实总归如此。“停滞”与“活跃”,“落后”与“先进”,是明摆着的。当双方不得不面对时,什么是更合情合理的方式?佩雷菲特没有基尔南(《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作者)激进。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表达上的差别。他们共同提出的问题,无法回避。且要在一个逻辑下理解:当人类无可避免地走向现代,其间发生的一切,后人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青年报) |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 建行客服
建行客服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