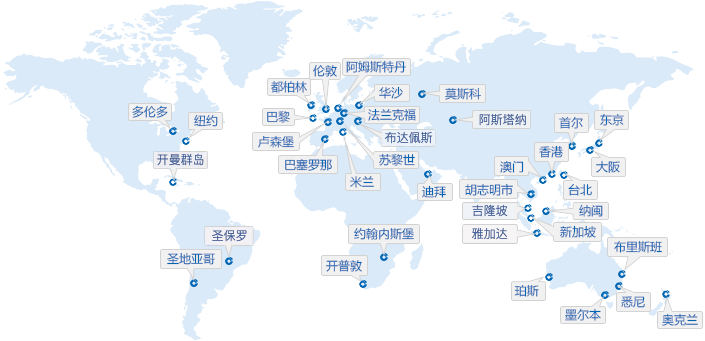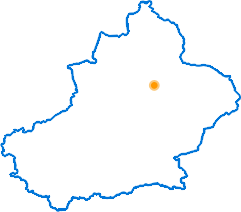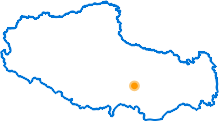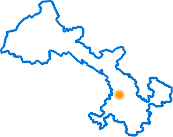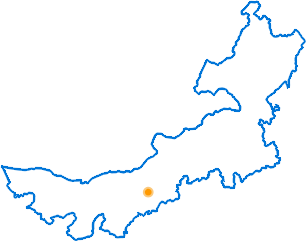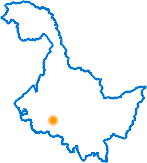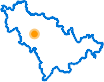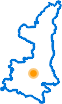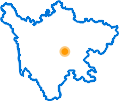|
韩松落最近发表了不少关于批评新《红楼梦》的文章,同时,他也能深刻理解贾宏声死前的绝望与落寞。而他真正担忧的,是“打造”出李少红和贾宏声的中国电影圈之大环境———当一个特色演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而无数导演都逼迫自己成为“百变星君”,这其实说明中国电影已经走入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 贾宏声直到去世之前都仍在寻找一个能让他再次燃起激情的角色。他为何失败了?是什么在阻止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电影人? 韩松落:正如水木丁所说,“其实贾宏声不适合演一些常规的、性格平凡普通的角色,他最适合的就是那些感情喷薄而出,能量巨大,令人震撼,个性鲜明,充满艺术气质,神经气质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的角色,大多数角色正常到近乎平庸。约翰尼·德普、爱德华·诺顿之类的戏疯子,在商业化的好莱坞可以被容,可以被鉴赏甚至被顶礼膜拜,在内地电影界却并无存活的机遇。内地电影的容纳性很差,不论是对角色,还是对演员。 很多人认为李少红并不热爱和欣赏《红楼梦》,但她却得到了拍摄《红楼梦》的机会。体现在中国电影圈也是同样的问题,大多数资源落在少数导演手中,而他们拍出的电影总让人感觉“不对劲”,这种“不对劲”或许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对自己手中的题材并不那么热爱,甚至并不擅长。 韩松落: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过于狭窄的商业片定义以及过于狭窄的商业片习惯。随便抽出一张北美票房榜,我们会发现,上榜电影的类型多种多样,动作片并非主流,家庭伦理乃至励志电影各显神通,“商业片”的定义非常宽泛。而内地的商业片类型非常狭窄,大多数时候集中在“动作”和“古装”上。这种过于狭窄的题材拥堵是怎么造成的?审查制度是一方面,比如古装戏不牵涉现实,容易获得通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影人的对面,只有一个完全虚拟的、根本没有摸底的“观众群”,他们性别构成如何,收入状况怎样,关注什么题材……中国电影人完全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们更愿意一厢情愿自说自话,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对“商业”的了解中,完全忽视对观众的针对性。当然,拥挤在固定的题材模式里,容易获得安全感。这种电影习惯,使得导演没有可能去拍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题材。 这反映了中国电影一个怎样的价值误区? 韩松落:烂片往往以“商业”为托词。但其实,“商业”应当是更为高级的艺术。内地商业片的题材风向标其实就是电视剧。某个电影题材热潮,往往是一段时间内电视剧题材热点在电影上的延续。这十年里的电影题材热点———古装武侠、宫廷斗争、战争片、谍战片,无一不是在电视剧领域先热起来,然后延伸到电影领域里,内地电影缺乏独立培育热点的功能,这也是一种信心匮乏的表现。 这种认识误区造成了什么恶果? 韩松落:过分依赖热点题材的结果是电影题材形成一种炒股式的板块轮动———一段时间里,一个题材会形成一种话语霸权,迫使资金、创作资源,全都涌入一个题材板块里,直到透支这个题材,然后,这些资源又像热钱一般流出,奔赴下一个题材板块,直到将新的题材“炒糊”。结果就是,内地电影没有较为恒定的题材脉络,电影人永远处于一种题材焦虑之中,不得不把自己培育成“百变星君”,努力适应各种和自己的风格喜好毫不搭界的题材样式。 在“贾宏声模式”和“李少红模式”之间,有没有一个相对更健康的模式? 韩松落:在正常的文艺环境下,一个作家一生中写的其实都是同一本书,一个导演一生中都在拍同一部电影。“宏大”和“百变”不是成就大师的必经之途。在自己的风格领域做到极致,就是大师。而目前的内地导演,显然失去了这个将自己的风格不断推向极致的环境。 程青松: 艺术电影在国内不能被认可,甚至没有正常的受众渠道,怎么就不能去国外参赛呢?电影节的评审会尊重那些表达自我的创作者。 韩松落: 约翰尼·德普、爱德华·诺顿之类的戏疯子,在商业化的好莱坞可以被容,可以被鉴赏甚至被顶礼膜拜,在内地电影界却并无存活的机遇。 贾樟柯: 如果只剩下娱乐,这也是一个很枯燥的世界呀。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观点我很认同,说的是最近电影界一直在谈“俗”是电影的一个特性,但假如是唯一特性,那就麻烦大了,就太偏颇了。(羊城晚报) |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 建行客服
建行客服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